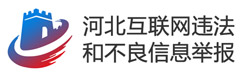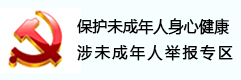文学史家袁世硕:古书与新意


袁世硕(右)与闻一多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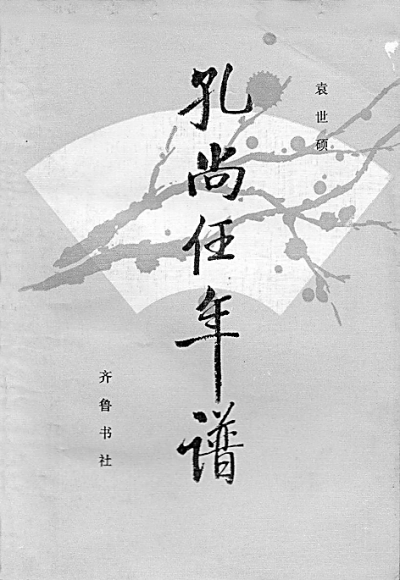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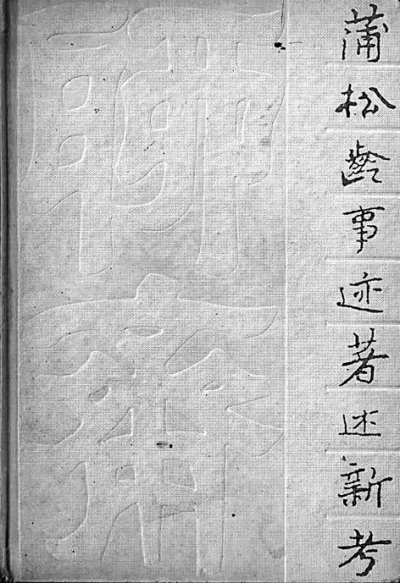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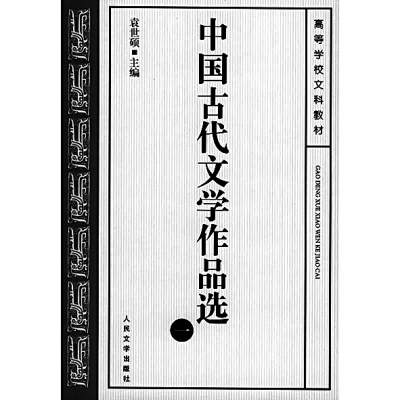

【大家】
学人小传
袁世硕,文学史家,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专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等职。现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20世纪50年代末,袁世硕广泛查阅文献,编写了极具史学价值的《孔尚任年谱》,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于1988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在国内外同行中获得一致赞誉,“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蒲松龄评传》《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敝帚集》;主编了《元曲百科辞典》、《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蒲松龄志》、《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第八编)、《中国文学史(马克思主义课程教材)》;整理校点了《清诗别裁集》,主持整理出版了《王士禛全集》;编辑出版了《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与严蓉仙合编)、《蒲松龄研究集刊》(1—4辑)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有影响的论文。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也是山东省社会科学首批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袁世硕先生,执教六十五载,岁月悠悠,他著作甚富却仍坚守躬耕三尺讲台,蜚声学界而从未放弃古典文学的钻研追求。袁先生始终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严格恪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在中国古代小说、古代戏曲及元明清文学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袁先生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多位在学术上饶有成就、在文化工作上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学生。
拓展通变
袁先生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冯沅君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谨严学风,在研究中注重从基本的训释古义、稽考史实做起,不凭主观臆断,不尚空言浮议。他坚信读古人书要“知人论世”,不赞成只就作品论作品的所谓“本体批评论”,但也不赞成烦琐的无甚意义的考证。
袁先生总是力求掌握最充分、最翔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的分析,搞清有关历史事实。例如,他曾细致地考察了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的许多小字注,联系《录鬼簿续编》中记载的罗贯中的行迹,论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末年。他通过对明嘉靖朝的权贵郭勋其人其事的考察,联系《水浒传》多写与大小权势者抗争的内容,以及写北方地理混乱、写南方地理较合乎实际的情况,论断这部小说绝不可能是出自武定侯郭勋或其门下士之手。武定府只是这部小说最早的刊行者。这类研究课题,对解决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解析古典戏曲名著《桃花扇》的创作起因和社会意义,20世纪50年代末,袁先生广泛查阅有关文献,编写了《孔尚任年谱》。这部年谱详细地呈现了孔尚任一生的行迹,着重考察了与他创作《桃花扇》有关系的一些人物,其中许多史实为已往的研究者所不曾涉及。此后多部《中国文学史》都曾援引其中提供的资料,作为评论《桃花扇》的立论依据。
即使取得如此成绩,袁先生并没有终止这个课题的研究,而是继续留心有关新文献的发现,斟酌原来的记述是否圆满确切。十几年之后,他又对《孔尚任年谱》作了增补修订,使其内容更加充实,对孔尚任在《桃花扇始末》中所言及的人物事件,全部做了考索分析,更加清晰地展示出这位杰出剧作家一生升沉荣辱之轨迹,以及因创作《桃花扇》而罢官的政治底蕴。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袁先生开始着手研究蒲松龄的著作,他广泛搜集、深入发掘有关文献,多次去蒲松龄的故乡淄川探访,到国内多所图书馆查阅图书,甚至东渡日本,阅览了东京庆应大学“聊斋关系文库”的文献图籍,搜集到了多种已往研究者未曾发现的珍贵资料。
在此基础上,袁先生完成了两项研究——
一是对蒲松龄的行迹、交游、著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索,揭示出许多后人罕知的隐秘情节。如从其挚友张笃庆的诗作,可知他年方及冠便已开始创作《聊斋》;从他曾与友人之妾顾青霞的交往,可以发现他对两性关系问题的新思考;从他在西铺毕家坐馆30年的生活状况,可知他何以能够坚持《聊斋》创作直至年逾花甲;从他与诗坛领袖、朝廷显宦王士禛的交往始末,可知两位文学家之间的真实情况等等。这些翔实的考证极大丰富了对蒲松龄的了解,也基本上搞清了他创作《聊斋》的具体过程。
二是对《聊斋志异》几种早期抄本和传世不广的早期刊本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基本搞清了它们各自的年代、篇章存佚、抄主情况,以及与作者原稿(仅存半部)相比较在内容文字上的差异。这既有助于探明作者原稿的全部情况,也为重新整理出一部《聊斋志异》的定本奠定了基础。
这些研究成果辑成《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由齐鲁书社于1988年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国内的《文学遗产》《文史哲》《上海社会科学》,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动态》《东方》,美国的《亚洲学会学报》等报刊都发表了长篇书评予以评介,称此项研究“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袁先生坚守传统的读其书须知人论世的理论原则,不仅注重考证有关作家的创作史实,也着意观察稽考作品的文体、题材、作法转化的实况,他考察作家的生平不停留于生卒、行迹、交游,更重视显现其性情与思想。因此,他的考证不仅细密,而且超越了一般的实证方法。他所著《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解识龚开》等,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问题意识
从袁先生的研究内容来看,自《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桃花扇》《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到这些名著的作者研究、意义阐释和传播研究,再到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评判,都表现出了他所倡导的“问题”意识。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之于《三国演义》,进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袁先生考察了由“尊曹”到“贬曹”的历史过程,指出《三国演义》表现的是宋元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遵循的是传统的道德标准。他认为,作为小说艺术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和政治谋略,具有极高的文学功能,不但不应否定,而且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借鉴。
对于《西游记》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如果仅仅从时代不同、读者观点不同去解释,即便做得十分周到仔细,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袁先生发现,明代中叶文学领域呈现出一股强烈的重情尚欲、反禁欲主义的思潮,于是对《西游记》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从取经故事的演化入手,运用历史和文化的方法,得出了如下认识——
玄奘取经的事迹,在通俗文艺中神魔故事化,原来弘扬佛法的主旨,逐渐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道教神仙进入佛教故事,内容便复杂起来,取经的主角发生了易位。到明中期受到了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浸洗,重新书写的取经故事发生了内在肌质的裂变,主题故事与具体情节描写表现出不和谐的倾向性,神佛有了世俗相,连同情节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揶揄、戏谑,呈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特性。
这就是《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以往批评家忽视了这一本质特征,用各自时代流行的观念,强行概括小说的主题思想,自然不合实际,难以自圆其说。
当袁先生较为细致深切地把握了蒲松龄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之后,再对《聊斋志异》进行分析时,发觉其中蕴含着蒲松龄的身影和心迹,最为明显的是那些叙写书生科举失意、诅咒科场考官的篇章。
由此,袁先生对鲁迅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聊斋志异》虽然不外乎记叙花妖狐魅之事,但与六朝人的志怪小说有着性质上的差异,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不是为了“志怪”,而是有意识地虚构狐鬼花妖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志,这些故事是表现思想的载体,内容具有了形式的功能。这与古代的寓言故事相似,要传达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寄寓的某种生活哲理。
袁先生认为,“红学”界在扬弃了“自传说”之后又发生了贾宝玉是不是“封建叛逆者”或曰“新人”的问题,于是发表了《贾宝玉心解》一文。他从正反两种意见中悟出:意见分歧的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小说人物贾宝玉的文学素质,贾宝玉不是写实小说中与现实生活中可以等同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中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向化的因素,如性情异于常人,说了些“囫囵不可解”却意蕴甚深的话语,曲折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灵。如果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准则品评其举止、话语,就失于胶柱鼓瑟,丢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称扬者隔靴搔痒,贬之者则难免迂阔。
古代文学研究历来有一个回到作品或作者本义的愿望,但是现在的研究者不可能回到作家创作作品的那个时代,所以,今天的研究只能用新的观念来诠释过去的文学作品,从而给出尽可能接近原旨的解释。只有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发展,民族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袁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验证了这一道理。新观点的提出,需要几个必备条件,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新方法的使用,三是观念的变革。正因为他以尊重历史的态度,从考证出发奠定学术研究的坚固基石,进而强调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才能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开拓和建树。
理论升华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文化思潮逐渐涌入,就文艺美学的理论与方法而言,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存在主义、现象学到语言哲学,异彩纷呈,目不暇接。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文化氛围中,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方法,袁先生既没有采取全盘接受的方式,也没有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主动接触,审慎辨析,汲取其中对于研究古代文学有益的内容,建构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发挥运用。他对于那些带有明显理论偏颇或者违反文学规律的观点进行细致分析,指出其学理上的缺陷与实践中的弊端,给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尝试进行中西理论的比较研究,使西方的灰色理论在中国学术领域焕发出绿色生机。
在学术实践中,袁先生娴熟地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史,从意识形态内部构成的诸种关系入手,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文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如对《聊斋志异》狐鬼精魅故事蕴含人生哲理的寻绎,对《西游记》神佛故事由宗教意识转化为审美意识的论断等,都体现了他的哲学思维功力和研究深度。
袁先生以《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玄言诗”为例,阐释了哲学影响文学、文学蕴含哲学的表现方式与深层规律。对于现象学美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体现了他关注作品本体价值的学术追求,这同只专注于考据史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研究有着明显不同。
袁先生特别注重诠释学的研究和运用,他从中国古代诠释学切入进行分析,体现了中西理论结合的特色,重点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历史客观性,指出文学诠释的本质属于认识,特别强调了历史主义是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并以《桃花源记》《三国演义》《圆圆曲》《红楼梦》等作品进行了具体论述,把理论辨析与作品阐释相结合,体现出理论服务于研究的鲜明倾向。
与此相关,袁先生还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行辨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从四个方面对伽达默尔的理论提出质疑:一是以游戏为建构其诠释学入门的论述,混淆了游戏与文艺作品性质上的差异;二是说文学作品是未完成事物,虽有一定道理,但否认其为客观存在则是错误的;三是作品的先在性,语言意指的稳定性,表明文学作品并非只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四是无视文学作品对理解的制约性,诠释的历史性便成为相对主义。
袁先生对西方接受美学三位理论家的代表观点——姚斯“期待视野”、费什“读者反应”和伊瑟尔“召唤结构”等核心概念也进行了深入解析,明确指出接受理论放逐作品本文、过度抬高读者接受(即文学消费地位)的片面性失误,紧紧抓住“作品本文”这个无论任何流派的任何理论家都无法绕开的核心概念,置接受理论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凭借理论的敏感、逻辑的严密与思维的清晰,袁先生排除了西式表达与翻译生涩造成的理论迷障,抓住问题关键和理论要害,进行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清理出基本的逻辑结构与推演脉络,最后破解其中的疑难并给予有针对性的理论匡正,充分显示了他的大家风范——宽阔胸怀、求实精神、兼容并包。
袁先生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耻于追名逐利。时常有同行、同事、研究生请他审阅文稿,他总是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帮助修改。作者要求发表时署上袁先生的名字,他认为侵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是不道德的事情,都一一婉言谢绝。
相反,袁先生从不把自己掌握的资料和研究心得视为己有,从不计较别人使用他提供的资料,或根据他讲述过的意见撰文发表。他注意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对研究生在业务上尽心指导,在生活上热情关怀,却坚持不让学生为自己办事,即使是查找资料、抄写文稿之类的小事,也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偶尔有之。
袁先生特别注意严于律己,行为端正,维持教师应有的尊严。尤其在学术问题上,他更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因此他培养的一批批学生,无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都能继承发扬恩师的这种精神,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作者:赵秋丽,系本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三届山东省政协委员;王平,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秘书长等职;冯仲平,系山东大学1996届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