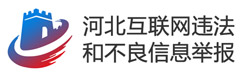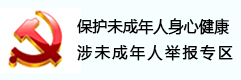从《司马迁》《李白》到《杜甫》 写历史剧观照当代人的心

话剧《李白》剧照,濮存昕饰演李白。
记者 牛春梅
前不久上演的北京人艺年度大戏《杜甫》,因为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杜甫而引发关注。对该剧编剧郭启宏而言,这也是他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环,从《李白》到《杜甫》,从“诗仙”到“诗圣”,他的诗之江湖完成了最重要的描摹。翻阅几十年来的《北京日报》,我们曾用一篇篇新闻报道和评论,记录着这位潮州籍北京编剧的成长之路,从京剧《司马迁》到评剧《成兆才》、昆曲《南唐遗事》,再到话剧《李白》《知己》《杜甫》,没有一部作品不曾受到关注。
■当初做编剧是“赶鸭子上架”
1940年,郭启宏生于广东饶平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家中接受古典文学熏陶的他,1957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市长彭真感觉北京市文艺团体创作者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因此决定从全国重点大学中招收优秀的毕业生充实各个院团的创作力量。工作人员先到北大、复旦、南开、中山、武大等高校摸底,了解哪些毕业生比较优秀,结果中山大学老师就推荐了郭启宏。
来到北京后,从没有看过一场评剧的郭启宏,被分配到了中国评剧院。对戏曲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的他,就被这么“赶鸭子上架”,服从分配当了戏曲编剧。郭启宏做学问比较老实,不会写戏那就多看。
剧院领导给了他一张月票,每天去中国评剧院管理的大众剧院看戏,剧院下场门有个放器材的小房间,就成了他的专属座位。“我心里想着党分配我干什么,我就要把它干好,一定要做一个好编剧,所以几乎每天都去看,同时还要看大量的书。”对郭启宏而言,戏剧的结构比较难,至于大家都很怵头的唱词,古典文学功底扎实的他倒并不担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启宏的父亲和哥哥双双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年仅48岁的哥哥戴着“右派”的帽子去世了,去世后几个月才被“拨乱反正”。哥哥的离去让郭启宏十分悲痛,父亲和哥哥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也让他联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知识分子,即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忍辱发愤,为中华文化留下灿烂的遗产,比如遭受宫刑而不改其志坚持完成《史记》的司马迁。
心有所动就奋笔疾书,郭启宏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出了京剧《司马迁》,因此有了“快手郭”的名号。身在评剧院,第一个原创作品选择京剧,是因为他觉得京剧的艺术形式更完整,演员选择余地也更大。作品通过之后,在只有9平方米的家里,郭启宏彻夜未眠,和妻子抱头痛哭,“那感觉就像是终于重见天日了。”
几经波折,这部作品被搬上舞台,一炮而红,获得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北京日报》1980年1月6日刊登的评论文章称这部作品“着力塑造了一个见识卓绝、善恶分明、刚直不阿、坚韧不拔的史学家的光辉形象。这是历史剧创作中的一个新收获”。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自发创作成为郭启宏的创作常态,他借历史抒发个人胸臆,成兆才、白玉霜、王安石、李煜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在他笔下“复活”。
■创作《李白》融入自身境遇
1990年,郭启宏调入北京人艺。一个戏曲编剧被调入话剧院团,可以想象当时北京人艺对人才的选拔不拘一格,而郭启宏也如鱼得水。对他而言,光写戏曲很难得到满足,“戏曲在反映生活的现实深度方面,不够丰富也不够尖锐,不能触及到本质的东西。”但戏曲程式化的表现形式也自有它的美,他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既能保持话剧的深刻性,也能有戏曲的自由。”
在北京人艺,郭启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院长于是之总是问他想写什么,大家可以出点主意。但习惯于自己创作的郭启宏不太习惯这种创作方式,只是摇头说还没有。其实,当时他正因为个人的境遇而决定写话剧《李白》。
李白被称为“诗仙”,留给人们的形象就是飘逸洒脱。郭启宏认为那是因为人们并不真正理解李白,“其实他没有那么洒脱,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在那样的社会里,有底线的人肯定就无法洒脱。”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话剧作品。
当他写完整个剧本后,交到了剧院。谁知道,于是之拿到剧本后,有半个月没有找他谈。毕竟是自己在北京人艺的第一个剧本,郭启宏心里非常忐忑。过后,他才知道那段时间,于是之无论去哪儿,随身都会带着李白的资料翻看。
有一天早晨,家人已经去上班了,郭启宏还没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刚刚晨练结束的导演苏民,一身短打站在门外。进了屋后,苏民就兴奋地说:“我看到了一个好剧本!”“谁的?”郭启宏问得有些心不在焉。“你的!”原来前一天晚上,苏民刚看完《李白》的剧本,就兴奋的不得了。对郭启宏而言,国学功底深厚的苏民,的确是导演《李白》的不二人选,已经退休的苏民也因为这个戏而重新燃起创作热情。开始排练前,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起沿着长江,重走当年李白走过的路,那段时间他们的话题只有李白。
今天再提起当年和苏民的合作,郭启宏坚持认为,“《李白》的生命力如此长久,有剧本的基础,也有导演的发挥,如果不是苏民执导,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和效果。”
转战话剧领域的郭启宏,第一部话剧作品又是一炮而红。话剧《李白》1991年年底公演,1993年即获得五项文华奖,包括剧目、编剧、导演、舞美、表演奖项,1993年11月27日的《北京日报》头版记录了这一重要时刻。纷至沓来的荣誉,不仅让郭启宏对自己有信心了,也意识到“北京人艺这个剧院能够实现我的追求,让我能创作出真正的杰作”。正因此,郭启宏不愿意由人艺之外的剧院来演他的话剧作品。他迄今为止创作了九十部作品,其中只有七部话剧作品,都是给人艺写的。
■写历史剧观照当代人的心灵
1995年2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人物文章中用一句话肯定了他的创作:在历史剧领域有“老郭小郭”之称,“老郭”指郭沫若,“小郭”就是郭启宏。
“写什么东西必须把自己摆进去,不把自己摆进去就没有真情实感,就没有创造性,没有反思……”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时,郭启宏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虽然他的作品中历史题材居多,但他认为,“历史不过是一个挡箭牌,历史题材也可以更曲折幽深地表达作者的个人愿望,艺术作品要是不能表达个人愿望为什么要去写?”正如他因为哥哥的遭遇写了京剧《司马迁》,因为个人境遇写了话剧《李白》,在他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投射着自己的影子。
书生气十足的他,常常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时,他写了昆曲《南唐遗事》。在他看来,李煜这样的人是当不了皇帝的,其悲剧在于错位的人生。后来他的话剧《天之骄子》中对曹植的勾勒,也是因为当过院长、下过乡的他,发现自己不是当领导的材料后,内心自觉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1995年1月28日,郭启宏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天之骄子〉创作刍言》中提到:“曹氏兄弟已经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他们的人生历程却被后世人无数次地重复着。我想起北宋清满禅师的一句禅语:‘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其实梁与柱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正是通过话剧《天之骄子》,郭启宏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可以做梁的做梁,可以做柱的做柱,不能做梁做柱的还能当柴烧”,他的心里也就轻松了许多。
大家都说郭启宏擅写历史剧,可他却觉得历史剧、现代剧这种只是着眼于题材的分法并不科学,“所谓的历史剧、现代剧,其实只是运用的材料不同,对编剧来说,创作方法、思维方式是不分历史和现代的。历史剧写的其实也是当代的事情,只不过是原材料来自于历史,其实抒发的是当代人的胸怀,编剧是当代人,观众也是当代人,不观照现实的历史不能给人的心灵任何影响,那就是失败的。”他将自己创作的历史剧称为“传神史剧”,重点在神而不是形,“我觉得历史只是历史剧的躯壳,灵魂还是剧作者要表达的对当代的思考。”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己也是知识分子,郭启宏的笔下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关注尤其多,他坦承,“写下里巴人不如写阳春白雪来劲”。他也以冷静的笔触剖析这个群体,“我爱知识分子,也知道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问题。”
2016年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国际戏剧节从北京人艺提供的众多经典剧目中,邀请了《知己》去圣彼得堡演出。在他们看来,这部作品写出了跨越国籍的人性,是俄罗斯观众也能真正看懂的戏。这部充满文人意趣和思想光芒的作品,正是郭启宏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一次深入思考。
回首几十年的创作道路,经历了那么多的起起伏伏,年近八旬的郭启宏慨叹,创作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但我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写,哪怕给很多钱。”眼下,他手里还有一部戏在写,“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从其中获得快乐,体现人生价值。我一辈子把这一件事干好了,就值了!现在看还行,我没有辜负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相关推荐: